明清之际西学汉籍整理出版的百年历程*
谢辉

谢辉(1983— ),内蒙古海拉尔人,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
摘要:从1911年至今的百余年间,学界对明清之际西学汉籍的整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国时期,其工作由大型丛书收录、宗教机构出版与学者整理三方面构成。第二阶段为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其代表性成果为台湾主要据海外藏本影印的约六十种国内稀见文献。第三阶段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此阶段的整理工作呈现全面繁荣的态势,大型专题影印丛书与点校本丛编,以及对专人专书的深度整理不断涌现,但也暴露出整理者重视西学,忽视传统文献学的问题。不同学科间学者的合作,应是下一步整理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关键词:西学汉籍;影印;点校
自明万历年间开始,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在传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的自然、社会、人文知识带入中国。在此背景下,一批以介绍西方知识为主的著作应运而生。这批典籍的作者或为传教士,或为中国士人,或中外合作;其著述的形式或翻译西方著作,或为新撰。但其所用语言则主要为中文,其出版的方式也多为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对于这批典籍,学界多称之为“西学汉籍”。西学汉籍自明末诞生之后,一度发展颇为繁荣。被称为“西士华文著述之第一书”的《天主圣教实录》[1],曾印至数千册之多[2]。有学者估计仅西学汉籍中有关天主教的著述,就多达千部以上[3]。尽管经过雍乾禁教等打击,这批典籍仍有不少流传至今,大致可分为基督教、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类。其中基督教又可分为圣经、神学、辨教、仪式、史传、格言等,此类文献在禁教运动中受损失最重,有学者统计,仅乾隆至道光间见于档案记载的查获天主教经卷案件,即有116宗[4]。但其总量较大,故存世独多,仅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所著录者,即有约160种之多。人文哲学可分为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学等,自然科学则可分为数学、天文历法、地理、机械、生物医药等。此类著述因有些传教士担心流于“玩物丧志”[5],冲淡其传教目的,故数量较少。但较受中国士人欢迎,且受禁教影响较小,清修《四库全书》,将《天学初函》中器编部分与附于理编之末的《职方外纪》收入,而理编《天主实义》等讲教理之书则摒之于存目,可见其态度。受此影响,这些人文与自然科学类著作,有很大一部分都流传了下来。钱存训先生谓明清时期耶稣会士的译著中“半数以上是关于基督教教义,三分之一是各种科学,其余是关于西方制度和人文科学”[6],目前存世的西学汉籍的总体情况,大致亦与此相符。近年来,学者对此批文献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新的整理成果大量涌现,成就斐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即对1911年至今百余年间,我国对西学汉籍的整理情况,分三个时期作简要回顾,并在此基础上略述其得失,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后续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

一、民国时期:明清之际西学汉籍整理的起步阶段
民国时期,古籍整理事业发展迅速,西学汉籍的整理也开始起步。这一时期的成果,可大体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以《丛书集成初编》为代表的大型丛书所收录者。据《丛书集成初编目录》所载,《初编》收录的西学汉籍,约有十九种,包括:《天步真原》、《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简平仪说》、《天问略》、《远镜说》、《经天该》、《远西奇器图说》、《职方外纪》、《坤舆图说》、《坤舆外纪》、《友论》、《几何原本》、《圜容较义》、《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地球图说》、《西方要纪》。其中前十一种为影印,其余为排印。其多用影印,可能是由于诸书图表较多,排印困难之故。从数量上来看,尚不足《初编》拟出四千种书的二十分之一,且受收书来源的限制,多为西方天文历算等科学类典籍,但在民国时期,仍是较有影响力的一大宗。此外《万有文库》亦偶有收录,但数量并不太多。
第二,天主教机构整理出版者。民国时期,天主教机构的出版活动较为活跃,较为著名者有:北京北堂印书馆、上海土山湾印书馆、河北献县天主堂印书馆、香港纳匝肋印书馆等。这些机构大多创立于清末,长期从事天主教著作的出版。而明清之际西学汉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是传教士入华时撰写的天主教书籍,这些典籍在民国时即主要由教会机构整理印行。例如,北堂印书馆在1913、1929年两次印行冯秉正《圣经广益》[7],1915、1919、1929、1933年四次印行苏尔金《圣教益世徵效》[8]。1917年《土山湾慈母堂图书价目表》,记载其在1914年出版徐光启《辟妄》、1915年阳玛诺《圣经直解》、1916年苏如望《天主圣教约言》等[9]。1924年《献县天主堂目录》,载其出版品中有1920年艾儒略《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庞迪我《七克大全》,1923年南怀仁《教要序论》等[10]。其出版的数量是颇为可观的。
由于天主教机构整理西学汉籍的主要目的,是用于传教,故其出版物多为天主教教理与西方神哲学著作,对于科技类文献则关注不多。即便是在教理著作方面,天主教出版机构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其出版的品种重复率较高,如庞迪我《七克》、利玛窦《天主实义》、冯秉正《圣经广益》等,在各地都曾多次出版。此外,还可能有随意改窜底本的问题。如方豪先生即将明刻本《天主实义》与土山湾、献县印本对勘,发现后二本对序言及内文均作了较大改易[11]。此二本虽然印于清末,但在民国大量重印,改易文字的问题也一直延续下来。但尽管如此,天主教出版机构的成就亦不容忽视,特别是在其努力之下,整理出版了一批稀见的西学汉籍。如北堂印书馆数次印行的《圣教益世徵效》,为清宗室苏尔金所撰。苏尔金为苏努之子,在苏努家族中最早接触天主教,其著作是研究苏努教案与清宗室天主教信仰的重要资料。然流传极稀,目前仅知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清抄本,且均为后人改写的白话本。北堂印书馆出版者乃文言本,很可能是自北堂旧藏的一个清抄本出[12],此清抄本今已不可见,幸有整理本保存其面貌。又如,北堂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高一志《民治西学》二卷,为高氏《治平西学》四种之一,亦据北堂藏清抄本排印[13]。此抄本今同样不可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另一抄本,但仅存上卷,故北堂印书馆排印本,为目前传世的惟一全本。此外,在整理形式上,天主教机构也有所创新。如朱星元、田景仙于1941年合编《文言对照天主实义》,由天津崇德堂发行。其书为两截式,上截为《天主实义》原文,下截为白话翻译。出版后颇受欢迎,1948年又重印一次,这在一定程度上,即是缘于其整理形式的创新。
第三,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所主持整理者。这其中成就较大者,当属陈垣先生。自1918年以来,其先后整理出版西学汉籍多种,主要包括:
《铎书》一卷。1917年,陈垣先生于徐家汇藏书楼见此书,欲录副而未果。次年,马相伯以抄本见寄,遂校勘付印。初版于1918年底印于山西,1919年6月重版,稍后又三版于溧阳,9月添入眉评,四版于天津[14]。
《灵言蠡勺》二卷。陈垣先生先于英敛之处得抄本,后又得崇祯间慎修堂重刻《天学初函》本,遂托樊守执细加比勘,于1919年印行[15]。
《辩学遗牍》一卷。英敛之先刊于《大公报》,后托陈垣先生整理再版[16],于1919年印行。有单行本及与《大西利先生行迹》《明浙西李之藻传》合订之本[17]。
《大西利先生行迹》一卷。此本所据者,乃徐家汇藏抄本,先由马相伯与英敛之校阅[18],后经陈垣先生校勘,于1919年与《辩学遗牍》等合订出版[19]。
《主制群徵》二卷。本书于1915年,由英敛之印行于天津,1919年再印,陈垣为之作跋。跋文中言:“末附《赠言》一帙,则清初文士赠若望之作,其诗为前印所未有,新从徐汇书楼抄得者。”[20]此谓英敛之整理本于卷末仅附录龚鼎孳、金之俊、魏裔介三篇贺文[21],而1919年重印本则“尚有名士赠若望诗十余首”[22]。此应是陈垣先生所增入,可见其整理之功。
《名理探》五卷。1917年,陈垣自英敛之处得一本,而英氏又得自马相伯。据后出的1931年排印本谓“徐汇书楼旧藏抄本,首端五卷,民国十五年,陈援庵先生转抄”[23],可知其源出自徐家汇藏抄本。1923年,陈垣命赵彬重抄一部,于1926年由公教大学辅仁社影印行世[24],为民国间最早刊行之本。


除了陈垣先生之外,民国间还有多位学者积极从事西学汉籍的整理,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例如,阎宗临于1941年,在《扫荡报》副刊《文史地》上发表《身见录注略》[25]。《身见录》为清人樊守义所作,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部中国人所著旅欧游记,仅有抄本藏于罗马国家图书馆,经阎氏整理,首次公布于世。王重民于1935年,在《图书季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海外希见录》,整理刊布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教皇致大明国国主书》与隆武帝、郑芝龙答毕方济诗[26]。其中《教皇致大明国国主书》为木刻印版,并不容易释读,而王氏即是民国时期较早关注并公布此文献的学者。向达则在1947年,整理出版了《合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此本以明福建刻本为底本,以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北堂图书馆、献县天主堂所藏五个抄本及陈垣校印本为校本[27],详注其异同,为民国时期西学汉籍整理的典范之作。总的来看,民国间由学者主持整理的西学汉籍,数量虽然不多,但多为流传稀少、学界急需之作,且校勘精良,有的还附有精到的考证。如陈垣先生在校印《铎书》时,即考其卷前阙名序文为李建泰作[28],此说后经黄一农补充考证,遂成确论[29]。举此一例,可见学者整理本之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民国时期,以上三个方面的西学汉籍整理出版活动,并非截然隔绝,彼此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是,《名理探》前五卷最早由陈垣于1926年主持影印,1931年,又由光启社整理,交土山湾印书馆印行。此后徐宗泽又托友人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影印得后五卷,并从北堂图书馆抄得卷前序言,合为十卷本,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编入《万有文库》出版[30]。可见在《名理探》的整理历程中,天主教机构、教外出版机构与学者都曾参与其中,由此也推动明清之际西学汉籍的整理工作不断迈向深入。
二、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以海外文献影印为中心
建国之后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明清之际西学汉籍的整理重心转到文献影印领域,其代表性成果为台湾学生书局于1965、1966、1972年,陆续影印出版了《天主教东传文献》初、续、三编。其所据之本,不少都来自海外,颇为珍贵,今详述之如下。
《天主教东传文献》(初编)收书六种,其中五种影印自梵蒂冈图书馆藏本。即:利玛窦《西国记法》(明末刻本,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27.7)、南怀仁《熙朝定案》(清刻本,馆藏号BARBERINIORIENT,132.3)、利类思《不得已辩》(清刻本,馆藏号RaccoltaGenerale Oriente, III, 225.1)、南怀仁《不得已辨》(清刻本,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27.8)、杨廷筠《代疑篇》(明康丕疆校刻本,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19.9)。另有《熙朝崇正集》一种,则影印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馆藏号 Chinois 7066)。
《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收书二十种,其中十五种影印自梵蒂冈图书馆藏本。包括:邵忠辅《天学说》(明邵氏自刻本,馆藏号Borgia Cinese, 334.7)、徐光启《辩学疏稿》(明末刻本,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13.10)、杨廷筠《鸮鸾不并鸣说》(明末刻本,馆藏号Borgia Cinese, 334.27)、严谟《天帝考》(清抄本,馆藏号RaccoltaGenerale Oriente, III, 248.10)、庞迪我《天主实义续篇》(明清漳景教堂重刻本,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23.13)、杨廷筠《天释明辨》(南明福州天主堂刻本,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21.2)、汤若望《主制群徵》(清康熙间刻本,馆藏号 Borgia Cinese, 324.23)、徐光启《辟妄》(清刻本,馆藏号 BorgiaCinese, 324.16)、罗明坚《天主圣教实录》(明末刻本,馆藏号Borgia Cinese, 324.1)、孟儒望《天学略义》(明末刻本,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13.15)、佟国器《建福州天主堂碑记》(清初刻本,馆藏号Borgia Cinese, 324.18)、利安当《天儒印》(清康熙间刻本,馆藏号Borgia Cinese, 334.9)、李祖白《天学传概》(清康熙间刻本,馆藏号RaccoltaGenerale Oriente, III, 213.12)、马若瑟《儒教实义》(清抄本,馆藏号BorgiaCinese, 316.20)、冯秉正《盛世刍荛》(清北京仁爱圣所刻本,馆藏号Borgia Cinese, 381.6)。另有方豪先生自藏五种,包括:艾儒略《三山论学记》(清道光二十七年重刻本)、阳玛诺《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正诠》(清末土山湾重刻本)、钟始声《辟邪集》(明末刻本)、杨光先《不得已》(1929年中社影印清抄本)、南怀仁《熙朝定案》(清道光间刻本,与初编所收之本内容不同)。
《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收书十四种,其中十一种可确定为影印自梵蒂冈图书馆。包括:卫匡国《逑友篇》(清初刻本,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23.8)、利安当《正学鏐石》(清济南天衢天主堂刻本,馆藏号RaccoltaGenerale Oriente, III, 247.3)、韩霖等《圣教信证》(清康熙间刻本,馆藏号RaccoltaGenerale Oriente, III, 222.10)、艾儒略《五十言余》(南明弘光元年福建天主堂刻本,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18.1)、李九功《励修一鉴》(清初刻本,馆藏号Borgia Cinese, 349.17)、、徐光启《造物主垂像略说》(明末刻本,馆藏号Borgia Cinese, 334.21)、高一志《譬学》(卷上,明崇祯间刻本,馆藏号BorgiaCinese, 364.1)、高一志《达道纪言》(明崇祯间刻本,馆藏号Borgia Cinese, 364.6)、王徵《崇一堂日记随笔》(明崇祯间刻本,馆藏号Borgia Cinese, 336.3)、高一志《空际格致》(明末刻本,馆藏号RaccoltaGenerale Oriente, III, 229.1-2)、伏若望等《痛苦经迹》(清初刻本,馆藏号RaccoltaGenerale Oriente, III, 214.7)。其余三种著作中,阳玛诺《圣经直解》为明末杭州天主堂刻本,经比对书衣所题拉丁文,及目录置于全书最后的独特卷帙编排,基本可确定影印自耶稣会罗马档案馆藏本(馆藏号Jap.sin.I.70)。高一志《圣母行实》为清康熙十九年广州大原堂重刻本,朱宗元《天主圣教豁疑论》亦为清广州大原堂重刻本,则来源不明。
除了《天主教东传文献》初、续、三编外,本时期影印西学汉籍的另一成果,即是于1965年由学生书局出版的《天学初函》。全书分理器二编:理编九种,如将附于《西学凡》之《唐景教碑》计入,则为十种;器编十一种,其中《测量异同》不见于卷前目录,《四库全书总目》以为“附于《测量法义》”[31]据卷前罗光《天学初函影印本序》,其所据之本,是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在民国时,为编纂利玛窦中国传教史,而向金陵大学借用者。后为其携归罗马,转交罗光代为保管。序言中谓“我乃函托罗马赵云崑神父计划摄影”[32],可知此本可能一直保存在罗马,未必前往台湾。其版多漫漶,故方豪认为“似系清初所印”[33]。
以上四种丛编类著作,共收录西学汉籍约六十种,自今日而言,并不算多,但在当时,却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西学汉籍的集中影印,为学界提供了大量急需的资料。如《天学初函》一书,传本稀少,英敛之“曾欲以重价收之,竟不可得”[34],陈寅恪亦曾致信陈垣求借[35]。特别是影印了一批以梵蒂冈图书馆为主的欧洲图书馆藏本,此批欧藏汉籍,之前仅有王重民、方豪等学者,在其文章中作过一些介绍,本次影印出版后,学界方得以睹其面貌。其中不乏有国内无传的珍稀之本,如《帝天考》《熙朝崇正集》等。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此四套书一直是研究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的主要资料来源,时至今日,仍然常常被引用。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其一,底本标识不清。《天主教东传文献》初编,除了最后一种《熙朝崇正集》附有顾保鹄、梁子涵之序跋,说明其底本与馆藏号,其余五部书都未作说明。《续编》加入了方豪所写提要,详细交代各本来源,梵蒂冈藏本卷前又加印馆藏号,比较完备。至于《三编》,既无提要,除第一种《逑友篇》之外,又不标馆藏号。实则底本的标识,在文献影印过程中至为重要。一方面,此批文献大部分来源于梵蒂冈图书馆,而梵蒂冈藏西学汉籍众多,一书而有多个复本的情况很常见,若不标明馆藏号,则不知所印者究为何本。另一方面,尚有少数文献为别馆所藏,若不说明,则更令人无从寻觅。如《三编》所收《天主圣教豁疑论》,梵蒂冈藏有两部,与其虽为同一版本,但比对之下,似细节均有不符,究不知其所印者是否是梵蒂冈藏本。如能标识清楚,则可避免这一问题。
其二,有影印阙漏之处。例如,《三编》据梵蒂冈藏本收录《励修一鉴》,检梵蒂冈藏原件,可知其天头原有刻印之小字批注甚多,而《三编》在影印时一概略去,致使内容损失很多。韩琦亦发现初编在影印《熙朝定案》时“漏印了个别奏疏”[36]。此外,《三编》据梵蒂冈藏本收录《譬学》,仅有卷上,但实际上,梵蒂冈亦存有此书卷下,只是将其编为另一馆藏号(Borgia Cinese,324.26),未与卷上置于一处。这虽非影印者之失,也终究是一件憾事。
其三,提要撰写偶有疏漏。《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卷前,收录了方豪先生为本编所收二十种书所写之提要[37]。方先生为宗教史学家,又长于文献之学。所写提要校勘文字、考证版本、讨论价值,均甚精当,但偶亦有失误之处。例如,其在《影印主制群徵序》中说:“是书原藏梵蒂冈图书馆……今日吾人赖科学影印技术之进步,获睹明刻本之旧,较前人为有福。”[38]是以此本为明刻。但今检其本,卷中避讳“玄”字,如目录“十一,以气之玄玅徵”[39],“玄”字与“玅”字之“玄”旁均缺末笔。梵蒂冈另有一本(馆藏号Borgia Cinese,370.4),不避“玄”字,卷前有崇祯九年李祖白《跋》与汤若望《小引》,版式行款与此本同,而字体有变化。对比之下,可知《续编》所收之本,实应为清康熙间翻刻本,所据者盖即梵蒂冈藏别本一系,而为避讳撤去了李、汤二家序跋。方先生以《续编》影印自明刻,并不准确。
但尽管存在着一些问题,此批文献影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也成为本时期西学汉籍整理的代表性成果。此外尚有一些零散的成果,如三联书店于1959年,据民国间《万有文库》本重新排印了《名理探》;文字改革出版社则于1957年,影印出版了法国金尼阁著《西儒耳目资》,收入《拼音文字史料丛书》中。但总的来看,仍以此次海外藏本的集中影印,在规模和价值上更为突出。
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西学汉籍整理的全面繁荣
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西学汉籍的整理步入了全面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整理工作,在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广泛展开,从整理的数量和质量上而言,都较前代有了大幅提升。其成果亦体现出以下四方面特色:
首先,大型专题影印文献的涌现。这一时期,比利时学者钟鸣旦、杜鼎克通过与海内外的学者及收藏机构的合作,推动了几次大规模的西学汉籍影印活动,包括:《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五册,方济出版社1996年),收录今存台湾辅仁大学的西学汉籍37种。此批文献原为徐家汇藏书楼所有,后于1949年被教会人士带往马尼拉,又辗转前往台湾,故仍以其旧藏命名。《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十二册,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收录该馆藏文献98种。《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二十六册,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收录文献191种。《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三十四册,台北利氏学社2013年),收录今存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的西学汉籍84种。此四部影印丛书,均由国外学者主持编纂,出版地也均在台湾。相比之下,国内学者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已有赶超之势。如2005年,由王美秀、任延黎主编的《东传福音》在黄山书社出版,收录基督宗教类文献380余部,其中约有70部左右的著作,属于西学汉籍范畴。2014年,张西平、任大援等主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全书四十四册,收录梵蒂冈藏西学汉籍170部。其余各辑亦将陆续出版,全部出版后,将成为目前规模最大的西学汉籍影印类丛书。此外,陶飞亚主编的《汉语基督教珍稀文献丛刊》于2017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目前所知较新成果,但在收录的十几种文献中,除《治历疏稿》一种之外,其余多为清代中后期至民国的基督教著作,故暂不列入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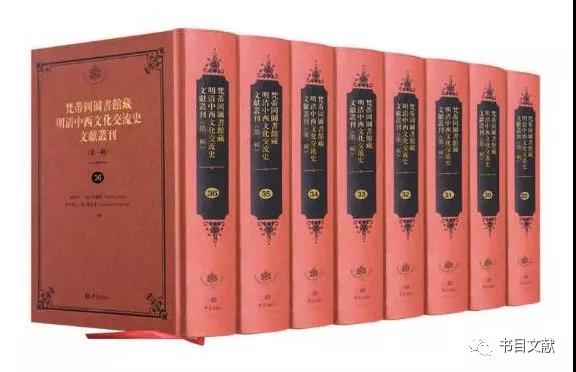
以上几部大型影印文献,合计收录西学汉籍多达五百多部,数量上远超《天主教东传文献》系列,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从古籍整理的角度而言,此批影印本收录的海内外图书馆藏本多较为珍贵,有的还收录了不止一个版本,这又为点校工作提供了底本和校本,为接下来的深入整理奠定了基础。
其次,综合类丛书注重收录西学汉籍。这一时期,在研究条件的改善和学界对研究资料的企盼的背景下,规模达数百上千册的大型综合类丛书纷纷出现。其在编纂时,延续了《丛书集成初编》等前代丛书的传统,将西学汉籍作为一个部分收录于其中。例如,《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收录了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杨光先《不得已》、汤若望《民历铺注解惑》、《主制群徵》、利玛窦《天主实义》、南怀仁《教要序论》等多部著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则收录了《四库全书》列入存目的十余种西书,包括《辩学遗牍》、《重刻二十五言》、《天主实义》、《重刻畸人十篇》、《交友论》、《七克》、《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西学凡》、《灵言蠡勺》、《空际格致》、《寰有诠》等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明代编》,收录了《西儒耳目资》、《职方外纪》、《浑盖通宪图说》、《西洋新法历书》、《几何原本》、《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泰西水法》等书。2013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子海珍本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珍藏子部善本》,也收录了毕方济《灵言蠡勺》、艾儒略《口铎日抄》两种著作。其收录的数量虽不太多,但充分表明学界已认识到,西学汉籍是中国古代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编纂此类兼收四部的大型丛书时,理应有其一席之地。
再次,西学汉籍点校本汇编的出现。在上述影印成果大量出现的同时,学界对西学汉籍的点校工作亦随之展开,特别是一次性点校多书的汇编类著作开始出现。此类成果中较为早出者,为加拿大籍韩裔学者郑安德整理的《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该书初成于2000年,2003年修订重印,共收录西学汉籍约60种,但仅为内部出版物,未公开发行。正式出版物中,以周駬方(一名周岩)《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为较早。该书于2001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线装五册,收录《辩学遗牍》等7部著作。2013年,又增订为《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新编》,除将《丛编》影印收入之外,又新增33种,使得收录的总量达到40种。继此之后,黄兴涛、王国荣又主持编纂了《明清之际西学文本》,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点校西学汉籍50部,其中《超性学要》、《穷理学》、《西洋新法历书》、《历学会通》、《新制灵台仪像志》、《律吕正义》6部著作为节录。同年周振鹤先生主编的《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收录著作30种,2017年又出版第二辑23种,包括多达三十余卷的《超性学要》。港台学者中,李奭学教授亦对《交友论》等17部著作进行了校注,编为《晚明天主教翻译文学笺注》,于2014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点校本汇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型影印文献利用不便的不足,部分详校详注者,更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最后,对某一书或某一人的著作进行深入整理之作纷纷面世。此类整理成果在上世纪末尚不甚多见,较知名者仅有数种,如谢方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之《职方外纪校释》,夏瑰琦点校、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年出版之《圣朝破邪集》,等等。2000年之后,此类成果开始大量出现。专门整理一书者如:陈占山校注《不得已》(黄山书社2000年),韩琦等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中华书局2006年),孙尚扬等校注《铎书校注》(华夏出版社2008年),黄曙辉点校《天学初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徐光台校释《格致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李奭学等整理《古新圣经残稿》(中华书局2014年),法国学者梅谦立等注《天主实义今注》(商务印书馆2014年)、《童幼教育今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吴青等整理《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齐鲁书社2016年),宋兴无等点校《穷理学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专人著作整理方面,较早者有朱维铮先生主编《利玛窦中文注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近年来又有李天纲编注《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笺注》(香港道风书社2006年),收录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三人有关西学的论著,肖清和亦编注有《天儒同异考:清初儒家基督徒张星曜文集》(香港橄榄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此外,暨南大学叶农教授近年来整理出版了《艾儒略汉文著述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澳门文化艺术学会2012年点校本)、《明末耶稣会士罗儒望毕方济汉文著述集》(齐鲁书社2014年)、《耶稣会士庞迪我著述集》(广东人民出版社、澳门文化公所2017年),其专人著作整理成果较为丰富。
与点校本丛编相比,单人单书的整理,在品种和版本的选择上更加精审,如《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据澳门图书馆藏稿本,《穷理学存》据北京大学藏抄本,在整理本面世之前,均为难得一见之书。而《天主实义》虽已有多个点校本问世,但梅谦立等《天主实义今注》,则采用了罗马卡萨纳特图书馆藏本作为校本,该本为《天主实义》目前所见最早的刻本之一,由此也进一步提高了校勘的质量。其整理形式亦不满足于简单的点校,而是进一步向着校注、笺注的深度发展,特别是一部分西学基础深厚的学者,能够对各书中的西方神哲学或科技内容加以注释,甚至连书中某段某句源自何种西方著作都能注出。这不仅使整理本的学术价值大为提高,更指出了西学汉籍作为一种特殊的古籍类型,对其的整理不能仅限于传统的方法与中文资料范围,而应兼取西书,中西合璧。其成果具有导向性意义。
总的来看,自二十世纪至今的近三十年间,西学汉籍的整理工作迅猛发展,其成果已远远超过前代。但与此同时,一些问题也开始浮现出来。具体可分为以下四点:
第一,标点文字错误。例如,《古今敬天鉴》:“御批诗曰:‘不显亦临昭,事上帝之心无时可懈。’”[40]此当作:“御批:《诗》曰:‘不显亦临。’昭事上帝之心无时可懈。”点校者盖误认“御批诗”为康熙御制诗,故下文以五字断句。《格致草》:“台小子志学是以合而重刻之,僭为之大,共名曰《函宇通》,以徧赞乎,为儒之有志乎参两者。夫重黎世司南北,正天明地,察我熊有初焉。”[41]此当作:“台小子志学,是以合而重刻之,僭为之大共名曰《函宇通》,以徧赞乎为儒之有志乎参两者。夫重黎世司南北正,天明地察,我熊有初焉。”“大共名”语出《荀子》。“重黎世司南北正”谓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此点作者已经注出,而仍未能避免标点错误。又如,《治平西学》“严鲁悔和未至悔也”[42],语不甚通。经查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鲁”实当作“曾”。下文“或问于其乐”之“其”字亦误,当作“基”。
第二,版本选择失当。例如,点校本《三山论学记》以《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收录之道光二十七年重刻本为底本,此本虽出于明代绛州段袭刻本,但不甚佳。如开篇首句“承先圣述造万主真传”[43],段本“万”作“物”,无“述”字,而空一格以示敬,均较重刻本为优。段袭刻本长期以来未经影印,2014年方收入《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此点校本出于其前,取用有一定困难,可以理解。但国家图书馆藏有段本原件,还是有条件加以利用的。《超性学要》以徐家汇藏本为底本,以《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影印梵蒂冈藏清刻本校之[44]。但书中未见有异文校记,绝大部分的校记都是底本刻印模糊或残缺,据梵蒂冈本补。可知二者应大致为同一版本,而徐家汇藏本的保存情况,尚不如梵蒂冈藏本,如径直改用梵蒂冈本为底本,则可省略大量无谓的校记。
第三,校改不当。此类问题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约略而言之:有应校而未校者,如《古今敬天鉴》“《大全》:震峰胡氏曰”[45],“震”字明为“云”字之误,“云峰”乃元代学者胡炳文之号。此文已明标出处为《周易传义大全》,一检即可知有误,惜点校者未能发现。有不应校而校者,如《超性学要》卷前胡世安序:“私智纷糅,灵承浊矣。”[46]据校记可知,“浊”字底本与校本皆作“独”,而底本上有批注:“疑为浊字。”按此处虽作“浊”字较通,但毕竟无直接的版本依据,改字似嫌太过,不如依前人批注,出异文校记为妥。下文“非天主有以抑扬之”,校记谓底本作“之”,据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改,则更不妥。因此处作“之”本可通,徐宗泽书晚出,不可为据。甚至还有在无任何依据的情况下,随意改易增删文字者。最为典型者即是《古新圣经残稿》,其书中包含着大量以方括号补入的文字,与以大括号删去的文字。如“女人瞧一瞧那树果子,[样子好看,]味大概[也]好吃,{样子好看}摘了一个吃了一半,那一半递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47],此句中第一处“样子好看”与下文“也”、“他丈夫”即为补入,而另一处“样子好看”则为删去。而这种改易的目的,竟然仅仅是“为求通顺”[48]。实际上,不作这些增删,原文未必不通,即便不通,亦属原作者水平问题,点校者无权擅改作者本文。此本是古籍整理中无须赘言的基本原则,而整理者竟不能遵守,以至于耗费大量精力,反而破坏了原书的面貌。
第四,注释不当。上文已经阐明,校注作为一种研究性较强的古籍整理方式,应用于西学汉籍领域,有助于揭示中国学者相对薄弱的西学内容,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但目前所见的几部校注、笺注作品,注释的质量尚有待提高。例如,《交友论》卷前瞿汝夔序言“即楚材希宪”,笺注者注“楚材”曰:“楚地的人才,亦泛指南方的人才。”[49]下引黄庭坚诗及《左传》为证。但实际上,此处“楚材”明应指元代政治家耶律楚材,与下文“希宪”所指的廉希宪,同为元代非蒙古族的重要人物。注者于“希宪”本已注对,而耶律楚材较廉希宪知名很多,出现此种错误实不应该。又如,《格致草》卷前熊志学序“《尚书》降衷受中之论”,注者于“受中”下注曰:“此处熊志学可能误认为‘受中’出自《尚书》,事实上,‘受中’出自《周礼》。”[50]按,“受中”之说虽不见于《尚书》,但亦非出《周礼》,而是来源于《左传·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语与上文《尚书·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一语,宋明理学家常用以阐发理气性命之说,故熊氏亦连类言之。其仅称《尚书》者,盖为与上文“大《易》资始资生”对仗,因行文之便而然,未必是误认。《周礼》中之“受中”,乃是受狱讼之成之意,与此全不相干。其余尚有大量不必要的注释,如注某干支或年号纪年为公元某某年,某字在语法上为何种词性,某字与某字通假等等,大部分都是常识性内容,读者皆能通晓,完全无必要一一注出。
以上四个方面,为近年来西学汉籍整理过程中较为集中且突出的问题。其余问题尚有很多,如在异体字处理方面,《古新圣经残稿》采用的方法是“各卷的异体字第一次出现时,以小括号加上正体字改之”[51]。实际上,晚明至清代的文献,其中的异体字多无关文意,不必保留,完全可以通改为标准的繁体字。若力有不逮,则一仍其旧,也无大碍。增加了此部分异体字的内容之后,全书大括号、厚方括号、方括号、小括号等各种校勘符号层见叠出,极为混乱,反有画蛇添足之嫌。《晚明天主教翻译文学笺注》与《天儒同异考:清初儒家基督徒张星曜文集》等,也都蹈此失。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罗列。
结语
纵观百余年来明清之际西学汉籍的整理历程,可以看出,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及表现出的不同特征,与学界对此批文献的认识程度息息相关。民国时期,尽管一些教会机构仍然延续清末态势,以传教为目的出版西学汉籍中的宗教类典籍,但一批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从中西交通史的高度,去阐释其价值。如梁启超即将明末欧洲科学类典籍入华,称为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的第二次接触[52]。王云五亦有类似论述:“我国汉译外籍,始于唐代之佛经。降至明季,耶稣会士来华渐多,辄与国人合作,翻译宗教天算诸书,旁及其他学术。”[53]在此背景下,才会有陈垣、向达、王重民等学者加入到整理队伍中。其间虽不无宗教因素,但更多的是出于学术的目的,如陈垣的整理工作,即是与其“研究支那与外国关系方面之对象”[54]的研究特色密不可分。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地位的认识更加清晰,如方豪即指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及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55]基于此种认识与研究的需要,以“搜求海外庋藏罕见的明末清初刻本或写本为最高目标”[56]的《天主教东传文献》等一批影印本,才会陆续出现。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学界进一步明确了西学汉籍的重要性与整理此批文献的急迫性:“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的‘天崩地裂’的时代,这一时期不仅有明清两朝的鼎革,还有入华传教士分别从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进入中国海域。此阶段的中国史已不能仅仅局限在本土内研究,而应放在整个世界的框架中加以考察。从文献学角度来看,这期间最为重要的中文文献之一,就是入华传教士来华后所留下的大批中文文献。只有将其系统整理之后,我们才能从中国和欧洲两个角度重新审视这段历史。”[57]而西学汉籍的整理,也迎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总之,西学汉籍整理的学术性转向,数量由少至多,形式由单一向多元,很大程度上是明清中西交流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史料领域的体现。
展望未来的整理工作,对珍稀文献的影印仍当为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首要任务。现存西学汉籍中,有大量国内无存者被传教士带归,流散于欧洲。尽管法国国家图书馆、耶稣会罗马档案馆等地的收藏已有影印行世者,然远非全部,另有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罗马卡萨纳特图书馆、法国里昂图书馆等大量馆藏没有披露。此外日本与中国往来密切,传教士经常将中国刻印的西学汉籍寄往日本用于传教,故日藏此类文献独多,至今未有系统公布者。对此批海外藏本进行影印,不仅能比较便捷地提供西学方面的资料,且在研究明清版刻、书籍流通等方面,也有价值。影印过程中,一方面应选择稀见的品种,另一方面也应注意不同的版本。因部分西学汉籍之各个版本,内容有较大差异,如传为徐光启所作之《辟妄》,其八章本、九章本与八章修改本之间,就颇有不同,对于研究该书之作者与流变有极大价值[58],影印时理应全部收入。此外亦应注重影印工作的学术性提升,特别是鉴于海外所藏的此类文献多未经系统的版本鉴定与编目,在此情况下,即不应简单刊布,至少应在版本等方面作出说明,否则将对利用者产生困扰。在此方面,西方学者主持的几部大型影印丛书即有所不足,而《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等中国学者主编者加入了提要,较为完善。在影印本的品种与版本都较为丰富的情况下,对西学汉籍的点校工作也应继续展开。但其形式不应仅为简单的标点,而应立足于深度整理,一方面以传统文献学的方法广搜善本,校勘异同,另一方面又从西学的角度,以笺注的形式,对材料的西文来源、西方神哲学与科学知识等加以注解。这要求整理者博通中西,既通目录版本之学,又明拉丁文与西方学术。一方不通,便至偏废。现有的笺注本多详于西学一方,而在标点校勘方面屡屡失误,即是明证。从现实的角度考量,似可考虑不同学科的学者分工合作,取长补短。未来随着古典学在我国的发展,一批如方豪这样中西兼通的学者将逐渐成长起来,而西学汉籍的整理工作,也将随之走入新时期,迈向新高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古籍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11&ZD109)。
[1]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作提要》,上海书店,2010年,第105页。
[2]利玛窦著,文铮译《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38页。
[3]李天纲《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史料与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页。
[4]张先清《刊书传教:清代禁教期天主教经卷在民间社会的流传》,《史料与世界》,第86页。
[5]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第2页。
[6]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文献》1986年第2期。
[7]JosephVan den Brandt,Catalogue des principauxouvrages sortis des presses des Lazaristesà Pékin de 1864 à 1930,Pékin :H.Vetch, 1933:p.17.
[8]JosephVan den Brandt,Catalogue des principauxouvrages sortis des presses des Lazaristesà Pékin de 1864 à 1930:p.14.雷强《北堂印书馆1931至1951年刊印书目考》,《图书资讯学刊》第10卷第2期,第158页。
[9]Catalogus librorum lingua Sinica scriptorumqui prostant in orphanotrophio T' ou-se–we, Changhai:ZI-KA-WEI,1917,pp.14,2,12.
[10]Catalogus librorum Typographi?Sienhsien,Xianxian:Missionis Catholic? TchelyMer.Orient:1924,pp.12,17,16.
[11]方豪《天主实义之改窜》,《方豪六十自定稿》,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1593-1602页。
[12]HubertGermainVerhaeren.Deux traités d’apologétique du prince Tartare Jean Sou-eul-kinLe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30, no. 362. Pékin :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1943,p.611.
[13]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14]陈垣《重刊铎书序》,《陈垣全集》第7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93-396页。
[15]陈垣《重刊灵言蠡勺序》,《陈垣全集》第7册,第408-409页。
[16]陈垣《重刊辩学遗牍序》,《陈垣全集》第7册,第410-411页。
[17]刘乃和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18]马相伯《书利先生行迹后》,《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3-224页。
[19]陈垣《大西利先生行迹识》,《陈垣全集》第7册,第412页。
[20]陈垣《三版主制群徵跋》,《陈垣全集》第7册,第423页。
[21]参见汤若望《主制群徵》,《续修四库全书》第1296册影印民国四年天津大公报铅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83-586页。
[22]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237页。
[23]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名理探》卷末《校刊识言》,上海徐汇光启社,1931年。
[24]陈垣《名理探跋》,《陈垣全集》第7册,第502页。
[25]阎守诚《阎宗临传》,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108-111页。
[26]王重民《海外希见录》,《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52-760页。
[27]向达《合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上智编译馆,1947年,第1-3页。
[28]陈垣《重刊铎书序》,《陈垣全集》第7册,第394页。
[29]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61-267页。
[30]徐宗泽《跋》,《名理探》,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582-538页。
[3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2003年,第1136页。
[32]李之藻《天学初函》,学生书局,1965年,第2页。
[33]方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51页。
[34]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947页。
[35]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第126页。
[36]韩琦等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第7页。
[37]初编所收六种书,方氏亦写有提要,但似未印入。提要见《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第2257-2272页。
[38]方豪《影印主制群徵序》,《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第19-20页。
[39]汤若望《主制群徵》,《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499页。
[40]白晋《古今敬天鉴》,《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第3册,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24页。
[41]熊明遇《格致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页。
[42]高一志《治平西学》,《明清之际西学文本》,第2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580页。
[43]艾儒略《三山论学记》,《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第3册,第611页。
[44]利类思《超性学要》,《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二辑),第1册,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9页。
[45]白晋《古今敬天鉴》,《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第3册,第131页。
[46]利类思《超性学要》,《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二辑),第1册,第15页。
[47]贺清泰《古新圣经残稿》,中华书局,2014年,第14页。
[48]贺清泰《古新圣经残稿·凡例》,第2页。
[49]利玛窦《交友论》,《晚明天主教翻译文学笺注》卷一,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14年,第14页。
[50]熊明遇《格致草》,第3页。
[51]贺清泰《古新圣经残稿·凡例》,第1页。
[5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9页。
[53]王云五《辑印汉译世界名著甲编序》,《王云五全集》第19卷,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67页。
[54][日]桑原骘藏《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
[55]方豪《中西交通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第692页。
[56]吴相湘《天主教东传文献序》,《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学生书局,1966年,第1页。
[57]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72页。
[58][荷]杜鼎克《徐光启是〈辟妄〉的作者吗》,《徐光启与〈几何原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5-304页。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3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谢辉先生授权发布。
(来自公众号:书目文献)